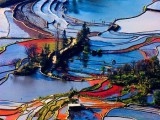中国在城镇化过程中面临的一个突出矛盾是:一方面是农村劳动力持续、大规模地转移到城镇非农部门,另一方面是农业用地分散在个别农户中,经营规模普遍偏小。无独有偶,日本与韩国在快速工业化与城市化过程中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回顾与总结日韩的经验对中国城镇化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从人均国民收入(名义值)看,日本、韩国分别在1974年、1988年跨过4000美元大关,中国则在2010年达到这一收入水平。日本城市化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初,1950—1975年期间城市化率从53.4%提高到73.8%;韩国城市化始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1965—1990年期间城市化率从32.4%提高到73.8%。两国经济均在这一时段起飞并得以快速发展,两国均注重农业发展日本在1961年制定被誉为“农业版宪法”的《农业基本法》,韩国在1971年开展“新农村运动”,着重进行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
日本的《农业基本法》目标是通过调整农业生产的经营规模分布,培育大规模农场,具体措施是放宽对农地占有面积的限制、鼓励农地适当集中,有步骤地推动土地流转,从而实现农业经营的规模经济,进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1970年修改后的《农地法》明确取消对购买农地或租用农地的面积限制,完全放宽土地流转管制。但是,推动土地流转的政策效果甚微:1980年70%农户的经营规模仍在1公顷以下,2公顷以上的大农户占比从1965年的5%仅上升到7.3%。导致这一现实的根本原因在于,兼业农户的数量迅速增加。以兼业收入为主的农户占比从1960年的32%增加至1980年的65%,越来越多的农户外出打工但仍保留土地,他们从事非农工作的收入占到家庭总收入的80%以上。
韩国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逐步放宽对土地流转的限制,1980年《宪法》允许农地租借和委托经营。1994年《农地基本法》进一步放宽土地买卖和对租赁的限制,允许设立100公顷土地面积上限的农业法人机构。但是,在促进土地流转的政策效果上,农业经营规模过小的矛盾也没有得到解决。
中国与日韩两国最大的差异在于制度不同,尤其是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和政治体制等。除此之外,有以下异同值得我们着重考虑。
第一,从城镇化水平看,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经济起飞时城市化率已经高达53%,经过20多年快速发展,至1975年基本完成城市化的使命;尽管韩国的起步水平只有32%,但到1990年,城市化率已经达到70%以上。反观中国的城市化率,在90年代只有26%左右,到2011年也仅为50.5%,刚刚达到日本50年代初的水平。如果按照非农户籍人口计算,这一比例目前仅为35%左右。这意味着,日韩两国是在城市化率处于较高水平的基础上全面推进土地流转,而我国目前仍处于城镇化高速发展阶段,是否已经可以像日韩那样推进农地流转?这需要我们深入研究。在此基础上,应认真思考以下两个问题:一是我国后续城镇化的动力来自哪里?日韩两国在经济增长率下降之前已经基本完成城市化,我国目前面临大量农村人口需要转移出来的压力,因此,推进城镇化首先需要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二是日韩两国全面推进土地流转的背景是务农人口比例已经很低(日本1975年为13.9%,韩国1990年为17.9%),我国现阶段务农人口占比为34%,这意味着日韩两国迫切需要通过土地流转来实现农地的规模经营,但在我国,这一压力显然低于日韩。
第二,从产业结构看,1975年日本人均国民收入达到5060美元,工业占GDP的份额为39.4%,服务业份额为56%;韩国在1989年人均国民收入达到5040美元,工业份额为41%,服务业份额为49%。比较来看,中国在2011年人均国民收入为4940美元,工业份额为46.6%,服务业份额为43.3%。在就业方面,我国现阶段服务业就业吸纳能力明显低于对应阶段的日韩两国:日本20世纪70年代服务业就业人数份额为50%,1989年韩国为45.3%,中国在2010年服务业就业份额为34.6%。因此,服务业滞后在短期内限制了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空间。
第三,日本与中国相似的农户兼业化现象背后的原因存在显著差异。日本农户80%以上的收入来自雇佣劳动收入,农户没有选择离农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日本在1971年制定的《农村地区工业引进促进法》鼓励将工业引向农村,扩大了农村就业机会。在中国,农村家庭收入构成中,年轻一代(20—39岁)在外打工收入与年长一代(50—65岁)在家务农收入各占一半,两者合计正好将农村生活水平维持在“温饱之上、小康之下”的区间,两种收入来源中任何一项缺失都将对农民生活与农村稳定产生负面影响。因此,中国农民选择兼业的原因并非是出于就近工作的目的,恰恰相反,他们候鸟式地到沿海发达城市寻找就业机会。
第四,中国与日韩的城市住房供给制度存在差别。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建成较为全面的公共住宅体系,特点是考虑了中低收入群体在房价快速上涨过程中可能出现购房返贫的情况。在实施方法上,日本规定新城区的开发必须由地方公共社团和公益单位实施,并始终坚持普通住宅用地开发的公益性和非营利性。韩国的《公营住宅法》旨在解决低收入阶层住房难问题,并在1988年推出《200万套住房建设计划》,成为韩国大力发展公共住房建设的转折点,有效扭转了户均自有住房套数长期下降的趋势。就中国来说,公共住房体系建设近些年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与人们的需求和期待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因此,在公共住房体系建设尚未成熟、城镇就业机会相对不足的情况下,如果快速推进农村土地流转,可能会增加产生“城市贫民窟”的风险。
据上所述,笔者认为,推进农地流转应充分考虑城镇化水平,应以城镇公共物品供应均等化为前提。在政策建议上,除继续深化土地制度、户籍制度、财税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的全面协调改革外,还应重点在寻找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以及加快公共住房体系建设方面着力。
(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型城市化视角下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研究”首席专家、复旦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