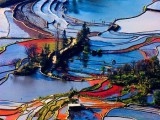农民富则国家盛,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村稳则社会安。农村土地制度是农村经济和社会制度的根基,与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纵观历史风云,农村土地问题关系到历朝历代的治乱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政权的兴衰。通过掠夺农村土地支撑城镇化的增长幻象,只会加剧复杂的国内形势。
农民富则国家盛,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村稳则社会安。正因为如此,在13个中央一号文件的表述中,三农问题从“基础地位”,到“首要位置”,再到“重中之重”。四个字的变化,释放了一个重大的政策信号,就是必须把农民、农业与农村放在各项决策的起点上,以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为抓手,作出自上而下的政策安排,从制度设计上走出以地生财的恶性循环,果断纠正先市民、后农民,先工业、后农业,先城市、后农村的思维定势。
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由来
很多人都认为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天经地义,对此提出疑义甚至改革就是大逆不道,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认识误区。党在根据地、解放区和新中国成立初期所制定的《井冈山土地法》(1928年)、《兴国土地法》(1929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1931年)、《中国土地法大纲》(1947年)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949年),都是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私有制。这些法律和文件还特别规定,有公共和军事需要时,政府必须按实际情况为农民换地,或按地价给予补偿。直至1956年6月,一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才规定了入社农民必须将私有土地转为集体所有,并在1975年、1978年和1982年的宪法中予以明确。梳理这样一个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到,从1928年到1956年的28年里,党所倡导和实施的农村土地私有制是一脉相承的。但在此后实行土地集体所有制的55年,争论和反复就一直没停止过。
安徽省小岗村农民当年按手印搞包产到户,本质上就是对土地集体所有制的一种叛逆和反抗。后来中央接受了这个事实,在全国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笔者在调研中发现,这个只有部分使用权的土地制度已经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比如按当时人口分配耕地,一定30年不变,搞大稳定小调整,新增的人口不分配,减少的人口也不退还。这就造成了全国普遍存在的外嫁女问题,以及2.5亿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为生活所迫涌向城市,他们种田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像候鸟一样在城乡之间迁徙流动。在他们的身后,还站着8700万留守老人、儿童和妇女。任何有良知的人都应该清醒地认识到,透支未来总是有限度的。没有什么政绩、增长或者发展,值得用这些人的命运去换取。现在,由于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农民就业不充分、失地农民利益补偿不到位所导致的群体性事件,越来越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导火索。这是一个必须抓紧而不能拖延的政治任务,回旋的余地越来越小。
解析高尔夫球场占地的制度缺陷
最近,高尔夫球场大量占地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农村土地制度的脆弱性。笔者所了解的情况表明,高尔夫球场已无处不在,从玉龙雪山到海岛天涯,甚至连沙漠也没有放过。全国有包括练习场在内的球场1000多个,已建的超过600个,在建的大约250个,列入规划待建的接近500个。按一个18洞球场通常占地1200亩计算,600多个已建球场共占地72万亩,其中占用耕地和林地28万亩。但问题不止于此,很多球场事实占地都在3000亩左右,个别球场甚至高达上万亩。这样一算,高尔夫球场占地已经超过200多万亩,占用的耕地和林地至少在百万亩以上。严重性还在于,今年上半年,国土资源部又接到涉及违建球场线索34个,恶劣的社会影响仍在蔓延。
其实,这恰恰反映出农村土地制度的缺陷。2004年初国务院就下发了《关于暂停新建高尔夫球场的通知》,此后高尔夫球场用地又历经十几次禁令,还被国土资源部、发改委列入《禁止用地项目目录》。按照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占地1050亩必须上报国务院审批。但为了回避这些环节,陕西省榆林市以“沙地生态公园”名义建起占地4000亩的沙漠球场;江苏省镇江市“绿色社体家园”变成占地4500亩的球场;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借口“新农业园”,在水利部沙棘开发管理中心九成宫科研示范基地建成占地7000亩的球场。不管是哪一种情况,农民都被强制性迁离他们赖以生存的家园,球场带给他们的只有泪水、恐惧和灾难。笔者认为,高尔夫球场明目张胆地曲线暴增,背后所隐匿的其实是挥之不去的腐败,是对农村土地制度脆弱性的警示。
从高尔夫球场占地的案例可以发现,因为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虚化了产权主体,农民不是自己宅基地和承包地(林地、牧场)的所有者,各级政府就借口“非经政府征地,任何农地不得合法转为非农用途”,肆无忌惮地侵占农民的宅基地和承包地。平心而论,房地产开发商在农民土地上盖起的高尔夫球场及其配套设施,一转手就有了“合法的”产权证。这是和平时期一种公然的掠夺,直接后果就是把农民整体上推向了城镇化的对立面。一个法制健全的社会,既要反对以非法手段维护非法利益,也要反对以法律正义干非法勾当。高尔夫球场2004年以后成为占地元凶,反映出地方政府把卖地作为主要财源已经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有钱者与有权者合谋,用银行撬出来的贷款支持土地几十倍、几百倍升值,预支了这个国家未来50~70年的土地收益。截至2010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2.7万亿元,同比增长70.4﹪。一些城市的卖地收入居然占当年财政收入的五、六成之多。这种一荣俱损的短期行为,造成了农民更加贫穷、农业更加困难和农村更加衰败。{Npage}
农民贫穷源于土地所有权缺失
笔者去过很多农民家庭,父老乡亲们两手空空,除了简单的生活和生产资料外,甚至连一件像样的贷款抵押物都拿不出来。农民为什么贫穷?穷就穷在没有稳定、合法的财产性收入。市场经济的前提是产权清晰,在土地所有制这个核心问题上树根不动,树梢白摇。换句话说,不挖这个穷根,用尽补贴、免税等办法也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笔者认为,土地高度集中、财富分配不均和贫富差距拉大等各种社会冲突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能用正确的方法及时化解。这就要求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必须正视主要矛盾。当前收入分配的复杂矛盾是城乡收入差距还在拉大,农民缺少工资性和财产性收入,靠种地过不上富裕的生活;产业发展的突出矛盾是农业基础薄弱、规模狭小、孤立分散,总体上还是靠天吃饭;社会治理的尖锐矛盾是城乡二元结构,失地农民所引发的群体事件成为最大的社会不稳定因素。
但让人深感忧虑的是,很多人直到今天仍然昧于国情,“拿农村的地、做城市的梦”,把农民排除在城镇化之外。有人形象地比喻说:“正在崛起的中国,有两块胸大肌特别突出:一块是城市房地产,一块是出口加工。这两块胸大肌之所以发育超前,是因为把农民的土地增值收益和农民工的剩余劳动及社保扣除当成丰乳剂,抹在了上面。”这个比喻道破了城镇化背后的真相,就是公开掠夺农村土地。笔者粗略地计算过,在近30年的城市化进程中,农民流失土地增值收入40万个亿。这是一个危险的博弈。纵观历史风云,农村土地问题事关历朝历代治乱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政权的兴衰。通过掠夺农村土地支撑城镇化的增长幻象,只会加剧复杂的国内形势。
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大会上指出:“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研究解决。”把土地所有权归还农民,就属于“不对的赶快改”一类问题。笔者算过一笔账,全国2.5亿个农户承包了18亿亩耕地,平均每个农户的经营规模大约为7亩,人均大约为1.39亩。但平均数不代表大多数,现在有14个省份人均占有耕地不到1亩,660多个县人均耕地不足0.5亩,也就是说这些省和县的农户经营规模更小。上个世纪80年代,小岗村农民用1年时间解决了温饱问题,但在此后的20多年里,由于缺乏资本聚集和现代科技应用的内生机制,这里至今没过富裕坎。事实上,自清朝中期以来,农业以传统村落为单元,农地零散化、细碎化耕作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
以渐进方式推进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革
有必要指出,如果不把土地所有权主动归还农民,就有可能被逼到墙角,想还都来不及了。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但每次自有规律可循。一个朝代建立初期,都注意痛定思痛,惩民之所恨,扬民之所善。一个朝代最终走向灭亡,也在于羽毛丰满后不再自我约束,各级官员通过各种手段疯狂兼并土地。自唐朝黄巢起义开始,后继的农民战争都相继提出了“均田地”的主张。如北宋王小波、李顺的“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南宋钟相、杨么的“等贵贱,均贫富”;明末李自成的“均田免粮”;太平天国的“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等口号,反映出农民对土地的强烈要求。事实上,近代中国革命从农村包围城市,也是把土地私有制作为政治纲领,以此鼓舞农民子弟为了自己的命运浴血抗争。
这些年来,笔者一直关注农村土地制度问题,曾经实地考察过100多个点,有很多切身的感受。国务院研究室第617号《决策参考》、光明日报第58期《知识界动态清样》、新华社第189期《国内动态清样》、中央党校第433期《思想理论内参》和中央政策研究室第204期《群言》,分别向中央领导报告了这方面的建议。笔者认为,现有农村土地制度的一个基础性缺失,就是长期以来没有建立有效的产权制度,表面上有多个代表,实质上主体模糊不清,农民处于弱势地位。这是全部症结所在。应当清醒地看到,1978年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恢复了农民对土地的部分使用权,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但国家对所有权的严格掌控,就不能保证农民对土地的忠诚。因此,要让农业乃至于附着于土地之上的林业、畜牧业真正完成产业化,前提是把土地所有权归还农民。
俗话说,有恒产者有恒心。农民意识到土地是自己的,才会珍惜和投资土地,放心自主地流转土地,这本来是一个常识。2009年9月,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农村土地制度有了一个重要的提法,就是对现有的土地承包关系要做到长久不变。从1984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土地承包期延长到15年,到1993年中央11号文件又提出15年到期后再延长30年,直至2009年提出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这是值得关注的亮点,意义特别重大。但两年过去了,对这一提法的批评不断。有人认为这是永佃制的现代翻版,还有人批评这是变相搞土地私有化。大概是由于这些干扰,到现在还没有看到怎样让土地承包经营权长久不变的配套政策。{Npage}
归还地权有利于城乡统筹发展
统筹城乡发展是科学发展观中五个统筹其中的一项内容,就是要更加注重农村的发展,解决好“三农”问题,坚决贯彻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逐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实现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实行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互动、协调发展。农村土地制度是农村经济和社会制度的根基,与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笔者在调研中发现,农村人口向小城镇集中的障碍,不在于户籍制度的限制,而在于农民不愿放弃作为福利的宅基地。这就打开了一扇门,可以在不涉及敏感的土地所有制前提下,把农民的宅基地使用权首先转化为可以有偿转让的产权形式,当农民选择小城镇就业或定居时,可以通过宅基地使用权获得相应的经济补偿,同时也获得进镇落户或创业的启动资本。借鉴这一步改革的成功经验,再考虑把农民所拥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改为完全的土地所有权,彻底解决产权主体不清问题。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应当注意有利于广大农民真正受益,避免分配不公而激发剧烈的社会矛盾。
可以预见的是,如果农村宅基地产权先行启动,一批有稳定职业和收入的农民工及其子女就可以就地进入小城镇,农村义务教育水平、基本医疗服务水平、公共文化体系建设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也因此会得到改善,从而提高我国城镇化的质量。现在,农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越来越低,农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从30%以上降到15%以下,并且继续下降。农民增收不可能通过传统农业本身解决,比较可行的做法,是以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革为契机,在小城镇首先着手,建设农业生产企业化、农民生活现代化和农村生态自然化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城镇化发展道路,是由本国特定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决定的。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最大的难点,但也正是希望所在。作为大中小城市与广大农村的结合部,小城镇是农业产业化的载体,是农民生产生活的家园,是推动新农村建设的基地。
从目前各地的城镇化情况看,原动力基本上来源于工业发展的用地压力,以很便宜的价格买断农民的宅基地与承包地,达到“占补平衡”。这种土地城镇化虽然拉动了经济增长数据,但大量农民进城却不能落户,建设城市却不能享受城市福利,被远远隔离在城市之外。在这种制度框架内,城市发展完全建立在农村作贡献、作牺牲的前提下,造成城乡经济发展、社会公共品供给以及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失衡。对于我国到底要不要发展小城镇,怎样发展小城镇,反对意见一直居上风。很多人对小城镇发展的影响、地位、功能和作用等问题因此存有疑虑,导致政策资源和资金资源分散,形成不了有效合力。国际上通行的“城镇化”概念,在我国也被片面地理解为“城市化”,形成了搀杂很多水份的城市化率。
农民是弱势群体,农业是弱势产业,农村是弱势地区,这一点已被大家完全认同。按照统计口径,我国有13亿人口,其中有9.4亿农民,农民占人口总量的70%,农业就业占就业总量的50%。这个基本国情,决定了要解决农民问题,就要保证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到位;要解决农业问题,就要大力发展非农产业;要解决农村问题,就要促进小城镇发展。统筹城乡发展要办的事情很多,但要分轻重缓急,既要讲量力而行又要讲尽力而为。笔者建议把农村宅基地所有权首先归还农民,推动这部分土地资源向县城和重点镇优化配置,实现土地升值、资本盘活和结构调整三大目标。这样做,既有利于小城镇发展,也有利于农民脱贫致富和新农村建设,可以说具有纲举目张的战略意义。准确判断这个大势,才能把握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走上由内需主导的常态增长轨道,处变不惊地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作者为北京大学中国地方政府研究院院长、台湾实践大学特聘专任教授)(彭真怀)